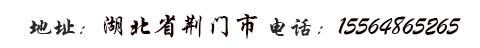宋濂论道处,诗人吟诗时
|
圣 寿 寺 圣寿寺与虚静斋 “真是一个清幽僻静之地啊,徐老师真是觅得一个遐思行文的妙处所在。” 12月27日午后,文研院采风团一行驱车来到城西夏演村的伏龙山脚,沿着弯弯曲曲的柏油路盘旋而上,经过两座石牌楼、步云亭、莲经亭、鼓楼,终于看到了青山翠色中的圣寿禅寺。但见寺院四面环翠、冈峦为障,寺前亭台楼阁临潭而建,亭桥相连、亭寺呼应,无不发出声声赞叹。 时值腊月,季入深冬,前些日子一直是阴雨连绵,寒冷萧瑟之感油然而生,然今日天气却是冬日普照,大家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之下,暖意融融,心情也变得格外豁达舒爽起来。正如文友们齐聚在圣寿禅寺边咫尺之遥的徐敢老师的“静虚斋”中的感觉一样。 说起这“静虚斋”,正是文研院创始人、现任理事长徐敢远离尘嚣,潜心创作的一个方外雅室。与这千年古刹毗邻而居,朝听晨钟,夕闻暮鼓,更兼环境幽静秀美,俨然身处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怎能不文思泉涌性灵合一呢?据说徐老师的好几部书,都是在这“静虚斋”中完稿的呢。 “徐老这是能掐会算啊,每次组织的采风活动都是这样的好天气。” “知道诸位今日大驾光临,老天爷怎么也要赏脸嘛。”风趣的徐老师说起话来总是让人开怀。 前世今生 谈笑间,徐老师便引大家来到圣寿寺门前,述说起这乌伤古刹的前世今生。一谈到这千年古刹圣寿禅寺,在如今年轻人的心目中或许是陌生的,对它显赫的人文历史,迷人的福地胜迹也就不得而知了。圣寿寺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距今已有多年历史。初名“龙寿寺”,开山祖师为凤林禅师。北宋治平二年,宋英宗赐额“圣寿寺”。元至正二年,高僧千岩禅师重建,大兴禅风于教,而成禅宗名刹。香火鼎盛时,圣寿禅寺有僧舍数百间,僧众近千人,甚至吸引了齐、鲁、燕、赵、秦、八番、日本、三韩、琉球等国内外僧众的奔走膜拜。历史上文人雅士和香客游人络绎不绝,著书颂扬,更有描绘其胜景的“飞泉吹烟梦,怪石参云水,遗然枯松根,瓮塔莓苔绿”之句流传,存有白乳泉、般若松、无尘殿、九松关、玉笋峰、洗钵池、瀑布崖、憩云亭、青松庵等众多人文景观遗迹。而这建寺于山腰的伏龙山,乃是龙门山脉的支脉,山西南起于兰溪,绵延金华婺城区和金东区北部与东北部的罗店、赤松、曹宅、源东等乡镇,东北达义乌至浦江而止,横亘数县。这一条起伏绵延于八婺大地的山脉,亦是一条文兴昌隆的文脉。黄初平、徐侨、艾青、施光南等的历史记忆都可登于伏龙山巅之上遥遥相望,而宋濂、黄溍、方孝孺等多位名人雅士更是曾到圣寿寺讲学论道,与当时的高僧千岩禅师结为“好友”,留下了诸多佳话。这些闪耀于历史的星空之中的文史印记,是义乌城西伏龙山中珍贵的历史宝藏。历史人文 文友们随徐敢老师缓步进入寺院,寺庙采用典型的三层式结构。最前面是天王殿,入内顿见高大威武的四大金刚在两侧把门。穿过天王殿,却发现新修大殿的钢筋混凝土地基不知为何已经停工,地基上长满荒草,砖石斑驳,许是停工时间已然不短。旧大殿的顶用蓝色的临时铁皮板房替代。主殿右边是居士楼,有人长住这里或参禅悟道或夏季避暑,价格也便宜,几百块钱一个月。一块古旧的石碑被随意地放置在居士楼的墙根边,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再往上走,就是第三层的三圣殿。 三圣殿右边那棵“千年罗汉松”格外引人瞩目,只见树的根部腐蚀中空,开裂成数片,如同叉开的手指,树身如打了蜡一般油光发亮,就似包浆醇厚的古老木器。而主干上两个挺拔苍劲的分枝却郁郁葱葱,如同两把利剑指向蓝天,堪称一大奇观。据树旁的碑文《古罗汉松记》介绍,这棵罗汉松已有多年树龄。年春,枯死多年的罗汉松竟重新萌发新枝嫩叶。后又枝繁叶茂,实为奇绝。据义乌旧县志记载,此罗汉松乃千岩禅师手植,誓言曰“此地若兴,吾松当茂”。 徐敢老师有感而发,随即赋诗两首,录此为记: 伏龙山行吟徐敢白鹭初临不言孤,青山绿水两相扶。香樟双拥迎新木,危塔独立断浮屠。登山粗望徐侨墓,入室细读望道书。宋濂归去应有悔,一代新人绘宏图。咏伏龙山下罗汉松徐敢放眼鹤鸣踏歌吟,松针支支书阳春。许身福地吻新泥,昂首苍穹笑浮云。细数千年风霜雨,权当临阵小热身。心雄不惧天雷激,一身傲骨一巨人。罗汉松的后面是祖师殿,墙壁已然千疮百孔,应是风化或者不知名的昆虫在墙上钻出无数的小洞,让这个看上去原本就不怎么稳固的小殿正加速度老去。祖师殿右侧有个小房子,据说是当时千岩禅师的住所。房子极其简陋,类似当时普通农家的柴房。 祖师殿大门边的两块石碑记载着千岩禅师的生平事迹:千岩禅师,俗姓董,名元长,字无明,号千岩,浙江萧山人。7岁时,经书过目成诵,出入循规蹈矩,有若成人。年稍长,即入寺院,从授经师学习《法华经》。19岁时于灵芝寺落发受戒,后谒中峰明本禅师。悟道后,首先隐于天龙之东庵,后因诸山争相劝请住持,不久便潜至乌伤之伏龙山。在当地信众的护持下,元长禅师在较短时间内便修复了久已荒废的圣寿寺,使之成为一代名刹。元主因仰慕元长禅师之道名,特赐元长禅师“普应妙智弘辩禅师”及“佛慧圆鉴大元普济大禅师”之号。元长禅师圆寂于大元至正丁酉年(),世寿74岁。临终有辞世偈云:“平生饶舌,今日败阙。一句轰天,正法眼灭。”遗有《千岩和尚语录》行世。 随后,大家举步来到寺外不远处的九层千佛塔,竟惊讶地发现佛塔已被列为“危塔”,围于一圈栅栏当中,塔脚满是掉落的砖石。谁会料想到,如今稍感破败的圣寿禅寺,在年前的元朝时,因为来了位叫千岩元长的禅师,会由一个小庙发展成连常住众也多达三四百人的壮观大寺呢。当年千岩元长禅师为躲避众多寺庙的邀请,杖锡逾涛江而东,行至乌伤(义乌)的伏龙山,见山形如青莲花,他说:“山若有水。吾将止焉。”话音刚落,便有乳白色山泉溢出,禅师便依大树而居。而今的一番景象,不知圆寂后的千岩禅师法眼观得圣寿寺现世,会作何感想呢? 千岩元长禅师圆寂于至正丁酉年,为他撰写铭文的是他生前好友宋濂。铭文里记载着他与禅师交往的故事,宋濂年少时,前往伏龙山拜见千岩元长禅师。见禅师气宇轩昂,吐字如雷。宋濂少年气盛,便想尽言辞诘难禅师,两人话不投机。过了两年,宋濂又前往伏龙山拜见禅师。禅师问:“听说您读尽大藏典籍,真有此事吗?”宋濂答:“当然是的。”禅师又问:“是用耳朵阅呢,还是用眼观呢?”宋濂回答:“用眼观。”禅师再问:“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宋濂扬眉向之,两人相视一笑,惺惺相惜,引为知己。自那次机锋相对的谈话之后,宋濂与禅师缔为可秉烛夜谈至半更的方外交,其文情厚谊延续三十余年。宋濂甚至为千岩禅师所植的松树作赞:“千岩大师于元泰定之冬,度涛江而来,憇止乌伤伏龙山。山有龙寿寺废基,大师遂缚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当兴,吾松其茂乎!’自时厥后,大师之道盛行,遂化瓦砾之区为伽蓝,松亦?长,析为二干,诘曲纠蟠,如虬龙夭矫,势欲飞动。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千岩禅师亦圆寂,呜呼!松虽植物,其有知兴衰死生之意者哉?”宋濂对千岩禅师,可谓是爱屋及乌了。文友们在这禅寺中边走边看,边思边谈,沉浸于圣寿禅寺静美的自然风景与深厚的人文故事之中,不觉已是日薄西山,冬季的太阳一下山,山中气温骤降,寺中响起了阵阵钟鼓诵经之声,缥缈而来,随风而去。 此时徐敢老师提议去他的“静虚斋”中用晚餐,师母已然备好饭粥小菜,还有贾良友夫妇与吴文军诗友带来的东河肉饼与上溪牛肉汤,大快朵颐。在徐敢老师书斋住所的露台上,文友们摆开桌席,露天而坐,几杯杨梅酒下肚,谈兴便浓,从古今笑谈到山野村史,从诗文词赋到文人轶事,丝毫不觉得冬季深山中的冷意,方兴未艾,忽然,我想起书里一段千岩元长禅师对话,兀自吃吃地笑了——有人见了寺里的猫儿,问禅师:“猫儿吃肉吗?”禅师答:“猫儿不吃肉,只吃老鼠。”那人又问:“那正知正德正道的人如何容得它?”禅师回答:“那你别来这里不就得了!”如今禅寺车马人稀,萧瑟破落不复往昔,正如猫儿吃老鼠,若容不得,别来这里不就得了!而我们这些文朋诗友们,就在这寺庙边喝酒吃肉,谈笑风生,若容不得,亦同此理! 附文友们即兴诗作: 歡聚聖壽寺 繆文中 古寺藏經典,群山隱沈羲。 亭台成景趣,塔影正相宜。 鳥雀聲聲喚,誰來他已知。 宋濂耕讀地,良友重逢時。 餅入書香意,湯溶讚美詞。 人文通今古,物道待展期。 禪鍾声声催,岂可再歸遲。 酒过三巡後,焉能不賦詩? 闻道圣寿寺 吴文军 空门访师入山林,松下隐约钟鼓音。 酒中言情真学士,话里家国含初心。 是非莫过十年判,学问总需万次寻。 醍醐灌顶开茅塞,闻道不觉夜露深。 游吟 季诚忠 最奇圣寿千年松,坚忍顽强是不同。 水秀山清文脉广,光风霁月入我梦。 冬访圣寿寺 黄选 古寺青山入深冬,老松残塔两三重。 霜钟暮鼓声相应,云阁寒潭影未浓。 阶苔乱生新雨地,石竹深罩旧禅笼。 只待满地山月色,今宵把酒今宵共。 古寺论道 黄选 禅门如屏翠连亭,一水寒潭步幽径。 九层浮屠嗟危立,千年寿松枯复新。 日薄古寺听钟鼓,夜临露台闻清音。 论道不觉空山冷,宋濂也羡我辈情。 长 按 关 注 图:季诚忠、缪文中、黄选 文:黄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lianmeia.com/wlmmjyf/17553.html
- 上一篇文章: 半期了,19年级要背诵的篇古诗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