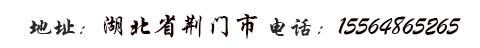日往烟萝八教九教十教二十六
|
(.10.13摄于东师) 周五上午的课是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中规中矩的课,老师也讲的中规中矩。早上八点五十七分的时候,幻灯片切到《相见欢》,站起来的同学索然无味地念到,“林花谢了春红”——在这个纯粹又沉静的暮秋清晨,我抬起头来,看见窗外橘缃色的叶子从高高的树尖哗啦啦地落下,划过干瘪的空气,摩挲出一阵阵焦枯的余味。我偷偷咽下抽屉里糅杂糯香的饭团,转头看向黑板,小声同她读起来,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语尾音落,我顷刻间撕裂成无数片酸楚的、决绝的、枯寂的漫天秋叶,蜷缩在途径漠河和大兴安岭而来的风里,漂流在伊通河和乌苏里江的水面上,我被风切割被浪拍打着要一路奔袭向南方去。 我的那一树南乔木早已枯败, 往日却烟聚萝缠,终日不散。 (一) 八教 大概就是上一个秋天。 晚上有天一的课。我和二羽在半更吃过饭,带着书坐在八教五楼大厅的椅子上。几近十一月,傍晚六点的夕阳饱尝万物,且迟迟意犹未尽。我身无考研压力,一本小说断续看了大半个月,依旧停留在半中不间的几页里。几行瞥过之后,又忍不住抬头看向大厅的落地窗外。 二十五教高耸伫立,明明暗暗的玻璃格窗有条不紊地吸收和反射晚霞,像是美国大片里镜头由远及近时,有什么大事要在高楼里发生一样。楼下是无数想要攀高却望尘莫及的叶榕、黄葛、香樟和银杏,它们或高或矮或蘩或疏地等待在校车经过的路边,风来了也像没看见似的,只是冷静持重地审视柳条懒懒地搭在崇德湖面上,冷笑一汪波澜不惊。 那段时间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ItneverrainsinsouthernCalifornia》,我像沉迷其他一切七十八十年代的旋律和嗓音一样无法自拔。男人在轻快的旋律里低沉又明朗地唱着“Itpours,man,itpours.”无奈而又释怀的语调携着秋天的气息从楼道里缓慢清润地渗透上来,我和二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小说内容,说着考研的进度,说着半更的红油抄手和蒸饺……说到晚课将始,才将书放进包里,起身走进教室 这样重复着,直至隆冬的某一天晚上。天一站在讲台上,用他自称文学院范围内相对标准的普通话说, “同学们,我们上最后一节课了哈。” 于是,从一首《白沟》开始,他从窦娥不冤讲到人生和家庭的幸福要义;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讲到势力对峙的军政韬略;从林冲刺配讲到所谓好汉怯懦自私的性格弱点……最后在对宝黛之情的质疑中,我们结束了同天一这短短的一程。最后一课上,他讲,其实90%的教育都发生在我们这些课堂之外。 后来我给他的短信里说,即使如此,但正因为有了你在课上教过的那百分之十,我才能在经历剩下百分之九十时努力地成长和学习,才想要保持初心地,不被那百分之九十中的荒唐、困扰或是喜悦的表象所迷惑。所以,你的那百分之十,真的很重要。 换谁,谁也教不了。 记忆里八教的课总安排在晚上,九点过的课结束后,人群鱼贯而下,却在走出楼门的一刻四散开去。朝着偏僻桃园走的人并不多,茂密的植物将夜色完全遮蔽,天低得快要碰上额头。 我听见前面走过去的几个女孩子在路上说笑,音色里还能辨出那些熟悉的、一晃便听了四年的声音:一股相声腔的老郭,语气不容置疑的小姨妈,狂放大笑的蔓哥,总是被开玩笑,永远在着急又娇嗔辩解的超英…… 我站在夜晚的田家炳路口旁,听见所有这些欢快、疲倦、高亢、肆意的声音从四面涌来,倏忽点燃冬天里已然潮软的柴堆。我又听见八方来风将它们一路携带席卷而去,我问风要把它们带向哪里,风说,沉入嘉陵江底,或是藏于缙云山中。 我让风走了。我留不住的容颜声色暗香疏影,风带它们去了好的归处。这是我在这里最后一个冬天的最大慰藉。 回头已经看不见八教的轮廓,只是它门前那株高大的蓝花楹在夜里绽放,片片蓝紫色的花瓣随风入夜。 我站在原地,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 (二) 九教 从前我最不喜欢九教,带着闹鬼的传说幽深曲折,进去以后分不清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就连自己身在几楼都不太清楚。可当相距千里之外的时候,它在我心里却悄悄萌生出别样的情致来。 要上课,必须穿过九教楼前逆折倒拐的走廊,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前右转,再穿过几间教室,再右转,再左转,然后走到楼梯前的尽头,那里就是上课的地方。前后的教学楼完美将整栋楼掩藏在其间,茂密繁生的藤蔓和乔木巧妙配合地势,夜里有与世隔绝的恍惚感,也许这就是隐秘藏在这幢楼一隅的教室独独令我恋栈的缘故。 大约亦是去年冬天的光景,晚上上课时天色已经很黯了,像大半瓶子的墨倒在低矮昏沉的游云间,窗外漆黑一片,窗上结起的一层薄雾,影影绰绰地映照着灯火通明的室内。杨全儿坐在讲台上,正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英国的东西真的很难吃,正同我们讲夏洛蒂勃朗特,讲狄更斯,讲巴尔扎克,讲契诃夫,讲席勒,讲惠特曼,讲陀思妥耶夫斯基…… 寒夜更深,在那个冬天那些夜晚和那一隅灯火的交织里,坐在教室里瑟瑟缩缩的我们,偶尔会冷不丁地接上杨全儿的话头,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又集体摆手偷笑着说:“没有没有……”那一刻的热烈喧嚣加厚了窗外的霜花,外面像是在酝酿一场大雪,而我们在此处围炉拥被,在隆冬的幻象中读海涅“星星们高挂空中,千万年一动不动”;读普希金“有人在思念我,在这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读雪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下课的时候杨全儿赶着去接孩子放学,我们在教室里道别后,将会重新走进曲折狭窄的走廊,在每一个尽头处拐弯,走过一段没有灯光的天桥一样的路,那段路幽暗晦涩,只能听音识人,尔或沉默如迷,尔或纵声笑语,绵绵缈缈,不绝如缕。 走过那段路,我好像一股脑儿撞破了次元壁,又回到尘世间来,举头银汉迢迢,回身再看时,九教早已埋在茫茫的风雪里,方才围炉温酒的噗噗声响荡然无存。 我挽起友人的手,留下背后幢幢虚无。雨果、拜伦、济慈、叶芝、聂鲁达,我统统忘了,唯独想起赫尔博斯的诗, “一朵玫瑰正马不停蹄地成为另外一朵玫瑰, 你是云,是海,是忘却。” 你是山间的皑皑白雪, 在我心头烈烈灼烧。 (三) 十教 回到最开始的那节诗歌研究课上去。 上午九点零八分,幻灯片切到《清平乐》。看见那句“更行更远还生”,倒真是“触目柔肠断”了。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把词照下来,不管不顾地发给兔叔,说着, “可以说是相当想你了。” 如果说天一代表八教,杨全代表九教,那么兔叔一定代表十教了。他出国前的最后一堂课上,我同14级的学弟学妹一起参加课程的期末考察,犹记得他出的其中一道题是孙光宪的《临江仙》——“终是有心投汉珮,低头但理秦筝。燕双鸾偶不胜情。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那天我刷刷地答完两道大题,交卷的时候既轻松又不舍,他在讲台上朝我边笑边说着什么,我也嬉笑着回应他,然后背起书包第一个走出教室。 秦筝,情真。走过蓝棚的时候,我心里忽然咂摸起刚刚写下的答案。脑袋里飞快地闪过许许多多零零散散且句读混乱的片段—— 从第一次领略他的怼人和白眼大法,到如履薄冰般提交第一篇读书笔记;从得到他一丢丢肯定就恨不得去全天下奔走相告,到后来被他嘲讽“人丑还不多读书”也心如止水;从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老祖宗们的八卦黑料,到写毕业论文时忍受他在大不列颠浪飞的炫耀…… 我曾以为大概我们之间的交集,顶多,最多,大抵就是如此了。但同样在离开之后,在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一节平淡无奇的研究生课上,一句“离恨恰如春草”,就能轻而易举让我坐回十教的椅子上,想着一会儿他会穿着牛仔裤背着包快步地走进来,说起: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就在我余生任何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这些字句、情境、欢喜、悲忧,都细润无声地同我所经历的春华秋月、金戈枯荣逐一暗合。 虽然这都要经历课上被兔叔抽背的恐惧,要经历和二羽靖羚在等校车的时候还在相互抽背“似花还似非花”和“东风暗换年华”的痛苦……可好在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如此美好,我将一生同这些山月古意长相守,同造语隶事相牵绊,同向我展开这幅画卷的人相连结,同我所涉足的每一处人间相契合。 十教就是这样一处无法被割裂出去的人间。记得大一第一次走进十教,说喜欢六楼的天台,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的课,都喜欢走到天台上远眺。白天可以看见露白风清,层林尽染,夜里可以看见万家灯火,缙云山的轮廓。在那个天台上,背过文学理论和教学概论,打过长长的思乡电话,也向夜婉拒别人,失神,离恨,迷惘,流俗,超脱,明澈、浑噩……大风刮过,纷纷开且落。 我又想起卷上的“秦筝”二字。试想我辜负了一切年华,但终究没忘记攥取一把秦筝。它弹出清冽却盛大的曲调来,我在纯想即飞与纯情即堕之间游走,最终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于是从十教顶楼的天台飞堕。下落的时候,我还能听见教室里传来我最倾心的调子: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今宵月明云淡,浓露未晞, 秋虫零星,却皆是我的羽翼。 (四) 二十六教和其它 二十六教周围有许多鱼尾葵。 晚秋时节最宜在二十六教北面尽头看日落。看太阳沉入群岚,看群岚湮于雾霭。在鱼尾葵自下而上枯败的日子里,适逢八月桂花香 红花酢浆草和乌蔹莓同爬山虎一起长在山崖上,遮掩着榕树的气根。我对二十六教没有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因为要在这里上的课,总是毛概马原之类,实在令人提不起兴致。从桃园走过来,总免不了一段翻山越岭,所以这里的课,能翘的都翘了,不能翘的也发挥主观能动性给翘掉了。 在二十六教上过的最后一门课,应该是“刘欢”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课堂乏善可陈,我们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前排坐着班上的弥足珍贵的三两个男生,老师的声音在偌大而稀疏的教室里格外渺远,而我常常在第二节课开始时从梦里醒过来,然后忍不住地问身边的曦狗和二羽, “咱们等会儿去杏园还是梅园吃?” 这几日,我脑海里总是重复同样一个场景。 今年六月的一个黄昏,我同曦狗和邓茹蓝从田家炳二楼走下来,她们说要去半更吃饭,我说我直接回宿舍了,然后我们在等校车的地方分别。就这短短的一幕,在我脑中不时被重播,重复着重复着,那一刻就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分别——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道别过吗?我觉得是的,一定是因为当初的告别不够用力,不够充满仪式感,我的心里才会长久地缺失了一块在哪里,想要用另外一个时空中的场景去填补。 今天说起这件事,我同她们讲,过去的好多事我都有些记不清了,如果再不能够写下来,怕是终究也散如流云。而身在北方过着食之无味生活的我,在将雪的夜里,却能够清楚地闻到干锅的味道:里脊和掌中宝在煨火上华光跃跃,油料已经极为入味,加热的哧哧声蒸腾上北碚的冬夜,单单佐以白米饭,就足以熬过所有阴寒。 还有不加汤料的鸡公煲,嘉陵江旁边的羊肉汤锅,以及在我最绝望的夜里予以热烈慰藉的骑龙……我的六识中只剩下味觉和嗅觉依然灵敏,依凭其一,也许还能再回到那里。 我偶尔觉得自己和老刘坐在沙坪坝的咖啡陪你说起彼此无人问津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偶尔又觉得自己和黄圣从没有路灯的彩虹桥走向五号门;偶尔觉得自己和二羽坐在城南24小时的便利店里聊通宵,我听着《萍聚》朝她呵呵直笑;偶尔也觉得还坐在北碚体育馆前的烧烤摊,老田把我面前杯子里的啤酒倒满,隔壁桌点了一首《男人花》,我把酒一饮而尽,急红了眼地问他,为什么总是我,他无言以对,望向十一点的末班列车。 明知时间开不回天生, 我惟有自斟自饮, 看陈事炽盛,因果互化。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 何如尊酒,日往烟萝。 (图片主要来自马丁的老相机侵删) 写于暮秋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lianmeia.com/wlmhxcf/643.html
- 上一篇文章: 景区深处园林景观植物大全后附图,
- 下一篇文章: 诗经里的植物们,到底长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