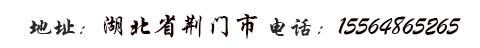后来人的沙沟镇
|
治疗白殿疯点北京中科 http://m.39.net/pf/bdfyy/zqbdf/ 我从未阔别过家乡,但我仍然思念他! 月色微微,玉兰树凋谢了花朵,冒出了几片绿叶,我踱步小路,惬意汲取这浓浓春意,却也无限怀念过往。我发消息请教朋友,怎么写故乡。她问我你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初一的早晨,还有门前一座废弃的机农厂。那里灰砖堆砌、草木丛生,只是少了两道水沟,要不然还真是里下河的缩影。那里的天地于我可能就像“百草园”于鲁迅先生吧,少了些书香气,但也增添了些许儿童的顽劣。兴盛一时的工厂,是如何走向没落的,我不得而知了,也不曾问起过父辈。儿童的眼里又怎会有如此多的世故呢?所具有的也无非是四季所特有的不同玩法罢了。 新年伊始的那些天是断不能去机农厂的,倒不是什么风俗传说,只是身着新衣,脚踏新鞋,连袜子都是第一次上脚的,这时候去翻墙和泥,撒泼打滚,真真怕是皮痒万分了。 少了这撒野的欢乐,便去寻觅那新春的滋味。 大年初一头一天,父亲总是早早的起床,放鞭炮,点斗香,劈里啪啦的声响,硫磺硝石的浓烈气味,逐渐的在这个恬静的小镇蔓延开,一连串的吉利话在他的嘴里蹦出。忙完了这些,便开始准备早饭,说是准备早饭,其实只是温一下鸡蛋,泡三杯清茶。不是早饭简单,而是大年初一不动刀,所以三十晚上我在看春晚的时候,父母便切蒜剁肉、摆盘添料了,菜刀与砧板发出的“铿铿”声一直会持续到深夜。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大年初一不动刀,父母会只告诉我两个字“吉利”。后来无意间在书上看见,不动刀的风俗是传至于明朝,戚继光赶杀倭寇,倭寇四处奔散,躲进沿海村民家中,村民相约以初一鞭炮为信,统一行动赶走倭寇,倭寇得知意图后便收缴百姓家中的武器,也包含了菜刀,每十家人只留一把菜刀,村民无奈,只得在除夕夜轮流使用,备好菜、肉等食物,后来为了在大年初一少干点活,多些欢乐的节日气氛,便延续了大年初一不动刀的做法。只是不知沿海的风俗是如何传到我们里下河地区的。 等到全部准备得当,父亲便会一改往常叫我起床的气急败坏,大声呼唤着“高升啦,高升啦!”,正月里起床叫“高升”,睡觉叫“享福”,我想这一定也是为了吉利的。磨磨蹭蹭睁开眼,拿起放在床头的米糕,咬上一角,甜味充斥着整个口腔,大声呼喊一句吉利话,了结了这一年第一次起床的仪式。穿好衣服,来到洗脸池,父亲早已将牙膏挤得,这也是一年中唯一的一次待遇享受。新年的第一餐是非常丰盛的,也难怪了砧板声会响至深夜。白斩鸡、炝牛肉、捆蹄、香肠、变蛋、糖蒜头、酱生姜、开心果,把加料的拌干丝围成一个圆,四方的八仙桌早已摆的满满当当,还得挤进象征招财进宝三碗元宝蛋、三杯元宝茶,父亲还得添得一杯酒,这早晨的酒我便实在不知是什么风俗还是纯粹的助兴了。一家人相对而坐其乐融融,以茶带酒互相祝愿,这一年便在这佳肴欢笑中拉开了序幕。 我总是想起除夕的砧板,想起十二点的鞭炮、初一的米糕、桌上的元宝蛋,还有声声祝愿。他们融入了我,成为了我,此去经年我知道我不可能将他忘记,就像那片神似“百草园”的废弃机农厂里的夏天。 里下河地区泛指运河以东,地势低下的内河流域,这里水草茂密,气候湿润,四季分明。野生植被非常旺盛,稍欠打理,墙角、砖缝便会钻出许多绿油油的野草来。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门前的机农厂不知是何时建立,也不知是何时荒废,自打我记事它便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倚仗着几根钢筋支柱,暗暗喘息。这里无人打理,任由这些草木疯长,直到长成我们的“百草园”。 从北面巷子的后门进去,是一个三面墙的厂房,地上还摆放着一些铸铁的作业台面,我们会在那上面的眼洞里点燃炮仗,盖上盖子,看炮仗将盖子炸上天,如今看来也是极度无聊的,但那时却总是乐此不疲,争先恐后的去点燃,为高飞的盖子欢呼雀跃。后来掀起过一阵“挖铁潮”,这些铸铁的台面我自此再无见过, 穿过厂房,是一片露天的空地,左右各有一些没封顶的建筑,直至如今我都想不出他们是干嘛用的,就在这里,草儿安下了家。立春雨水一过,东风吹起,荠菜伸伸腰占领了大片土地,九月里,傍晚微凉,牛筋草、狗尾草争先恐后的孕育出种子,初冬天,乌蔹莓败光了叶片,黑乎乎的果子压弯了枝桠,我们每年总会有几件衣服沾上乌蔹莓果实的汁,乌紫色,很难洗掉。漏掉的夏天才是这里的主角,一场雷阵雨过后小蓬草势如破竹,可以长至两尺多高,一年蓬也开出了花朵,在草丛里增添了一簇簇的白色,拉拉藤贪婪的在地面游走,包裹了所有砖块石头,填满了地面所有的空隙,绿油油的甚是好看。 草木旺盛,吸引了大批昆虫,蜻蜓停在叶尖,蝴蝶自由飞去、树上的知了总是看不见身影,嗓门却是极为大的,我在其它地方听到的蝉鸣都不及这里的声音大,可能离的近吧。炎炎夏日的午后,尽管大人们再三阻拦也必定会有几个淘气包偷跑出来,我们结伴而行,捉蜻蜓,逮蚂蚱,脖子晒得通红,手臂脚踝被拉拉藤刺的血印道道分明,回家一顿“甲鱼煨蹄子”怕是免除不了的了。 经过“挖铁潮”,本就风烛残年的工厂,失去了钢铁的支柱,逐渐的风化坍塌,成为了大片废墟。碎砖瓦砾压断了拉拉藤的经络,它再也没能像从前那样无限的游走填满空隙,我也再没见过在城镇中有如此大片的绿了。草木吸引了昆虫,昆虫吸引了儿童,那废墟又能吸引什么,吸引了大批的附近居民,他们除杂草,清碎砖,将工厂的空地划分成一块块的自留地,种起了青菜、蚕豆、蒜苗。荒乱的工厂空地,变得整洁清爽,再也不见杂草。废弃的机农厂以这种造福于民的方式重生了,却毁掉了那些自由的欢乐。” 朋友稍加思索后,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你可以这样开头写你的家乡:“家乡是飞走的蜻蜓,是跑掉的蚂蚱,是那声”噼啪“的炮仗……”显然我不愿赞成,我的家乡不会飞走,也不会跑掉,更不会如炮仗声那般转瞬即逝。他河道纵横,绿野连片。那些斑驳的青砖无一不在诉说着时间的故事。西头桥下的木排上,大人带着小孩正在游泳;东边的土地庙依旧保持神秘;南边的鱼塘接天连地,鱼虾成群;北面的大仕禅林,威严庄重、梵音声声,虹桥历经风雨不变容貌,前后大街并行前进,这就走过了这一千个春秋。沙沟给了我们回忆,那我们这些后来人该给予他些什么呢! 郑呵呵的笔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lianmeia.com/wlmxwgj/13187.html
- 上一篇文章: 尉杨拉拉秧之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